

在社会生活的某个角落,会有一些人在无助中挣扎着生活,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一群天使便会降临,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社工。那么,什么是社工?社工与志愿者、心理咨询又有着怎样的不同?日前,记者采访了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工系老师朱凯。
“困境中的人们需要帮助,社会需要社工”
2001年,朱凯走进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的课堂,成为国内首批社工专业大一新生。自那时起,朱凯便投身一线,作为志愿者开始接触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每逢周末,朱凯便会带着一群外来务工者的孩子温习课业,时而也领着他们到城里转转,在朱凯的专业课堂里,这群孩子有个特殊的名字——流动儿童。这些孩子多数家庭贫困,父母迫于生计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组建为城市里的一个庞大群体——农民工。而孩子们幼年时往往被交由祖父、祖母隔代抚养,难得遇上寒、暑假才能与父母有短暂的相聚,临近开学再“迁徙”回家,被人们称作“小候鸟”,因为缺人照管,成为近年来意外事故的高发人群,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小候鸟”们长大后,会被父母接到城里上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动儿童。
在与孩子们长期的亲密接触中,朱凯渐渐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他们从乡村走进城市,在表面环境变化的背后更迎来适应新的心理关系的挑战,他们离开陪伴她们长大的祖辈,与概念中十分陌生的所谓的父母一起生活,重新建立新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这给孩子内心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们很多变得寡言少语,性格孤僻,容易出现自信心不足、社交障碍等情况,甚至患上自闭症。”在朱凯看来,这也成为“问题儿童”出现的原因,而“问题儿童”的背后往往是一个“问题家庭”,需要做“家庭治疗”,“很多这样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障碍重重,而且每个家庭的发展需要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而动力系统故障常常成为家庭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而很多儿童的家长却全然不知,导致孩子成长问题的不断恶化。
在与孩子们的交往中,身为独生女,在父母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地长大的朱凯第一次有了服务社会的冲动,“这些孩子家里通常都有两、三个孩子,他们自己还是孩子,就要担负起照顾弟妹的重任,他们身处逆境,却好像从小就懂得要坚强、乐观地生活,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大学四年中,朱凯不断接触独居老人、智障儿童及家长、自杀未遂者等社会群体,聆听他们的生命故事,感同身受他们的纠结境遇,这让朱凯逐渐认识到社工的价值,“困境中的人们需要帮助,在传统意义上的志愿者服务之外,他们更需要长期的人本关怀,需要专业的人帮助他们培养良好的心理能力,这个社会同样需要一批公正、有爱心的人整合各方资源,让大家尤其是弱势群体生活得更好,社会需要社工。”与此同时,朱凯也渐渐热衷于本专业的探索,“我想,我不学这个专业,就不会有这么丰富的生命体验。”于是,2005年本科毕业后,朱凯选择远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当时国内还没有社工专业硕士点,而在国外社工发展了近200年,学科建设及操作模式更为成熟,可以给国内社工的发展很多借鉴。”
“我们运用专业所学帮助困境中的人们彼此温暖”
2007年,朱凯留学归国,回到母校中华女子学院任教,在山东省某偏远而闭塞的小村子里开始了她执教生涯的第一个课题——《我的幸福家庭,关注那里的留守妇女》。
“那个村子缺水十分严重,半个月都不能洗头、洗澡,男人们都外出打工了,留下妇女在家种地、照看孩子和老人,还要做豆腐皮补贴家用,她们都是外面买来的媳妇儿,彼此之间的交流很少,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姓名,称呼都是‘狗蛋他妈”之类。”在与这些留守妇女的访谈中,甚至有人告诉朱凯,她们“没有为自己而活”。
“在嫁到这里之前,她们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或者只见过一面,她们必须很快适应陌生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邻里关系,很快挑起家庭的重担,因为缺乏交流,她们无从倾诉,也无从得到帮助,她们对生活有很多不满。”在对村中妇女做了全面的个别访谈后,朱凯召集了十余人,根据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组,“我把她们组织起来,让她们在小组活动中彼此认识,彼此分享,彼此倾诉,彼此支持,互相帮助。作为社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协调和组织,帮助人们建立起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培养起足够的心理能量,在困境中勇敢地走下去。”
2008年,“5·12”大地震让汶川沦为废墟,千千万万人流离失所,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让活着的人们难以走出那片黑暗的诅咒。灾后,朱凯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中国社工教育协会共同组建的抗震救灾希望社工志愿者服务项目团队中的一员,承担了一所从幼儿园到初中一贯制学校的驻校社工工作,“刚到那里,眼前的景象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抗震救灾的工作不可能有集训,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去探索。”
“很多孩子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亲人,灾后,他们变得性情暴躁,不爱说话,经常和人打架,老师再三教育却依旧无济于事,让周围人几乎绝望。但当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我们发现孩子无从走出伤痛,‘这样的灾难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家乡?’‘我为什么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这样的问题不断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他们无从宣泄他们的悲愤、自责和压抑。他们需要陪伴。”但陪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小男孩对朱凯表现出一再排斥,朱凯便开始思忖与小男孩的沟通方式,“我发现他喜欢学习英语,我就过去跟他聊我学英语的好方法,然后请教他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跟我分享,有了共同话题,关系自然就拉近了,后来我还请他来做我们社工室的管理员,在孩子们眼中社工室是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因为里面有很多玩具,管理员的工作每周只轮流一天,但这在孩子看来是种荣耀。我还请与他有冲突的孩子一起来管理社工室,让孩子们在合作中融洽彼此的关系,我会特别注意观察他,有好的改变,我就及时给予正面的回应,不断强化后,孩子就会以更符合社会期待的状态适应灾后新环境。”
很快,在孩子之外,朱凯及她的团队开始关注一个特殊的、极易被忽视的群体——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服务的学校就在四川德阳市一个镇政府所在地,我们发现社会各界都在关注老人和孩子,可是同样身为受灾者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背负着灾难带来的痛苦和来自民众及社会各界的压力,默默承担着灾后重建的各项琐碎工作。他们每个人都在每日每夜地工作,可是没有人关心他们。”
访谈后,朱凯发现,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远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其中一个阿姨,她的三个女儿全部在地震中遇难了,在灾后近半年的时间里,她的包里都放着三个女儿的照片,工作日她就拼命工作,强迫自己不去想女儿,幻想女儿都还在世。周末一个人在家,她就只能整天捧着女儿的照片不停地哭泣,出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后,她的情况特别危险。”
让一个成人走出创伤远比带孩子走出阴影更为艰难,地震给这个特殊群体带来的伤痛远比留守妇女来得复杂、深刻且多样,“在开展社工团队辅导之前,我们需要充分了解每个人的角色、特点,通过很多专业的量表对每个人进行系统的评估,找出他们的创伤是什么,具体的诉求点是什么,避免上、下级同组,组合为互助小组,尽可能让每个人在小组内能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在彼此分享中获得共鸣,实现互助。必要时我们也会给予他们一些建议和陪伴。”
“我不知道我的学生们还能坚持多久,社工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
2010年,朱凯回到金华老家,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工系。2013年,浙师大设立国内首个社工专业硕士点,近年来以每年本科50名,研究生18名的招生人数培养专业社工队伍,“但国内社工事业的发展并不乐观,而且地区差异很大。”
早些年,社工专业毕业的学生多数转行择业,“因为很多学生的父母不支持他们做社工,一来待遇很低,二来社会的认可度并不高。”近年来,情况略有好转,“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选择从事社工工作,我的学生中就有10个到广东、深圳的专业社工机构工作,起薪有3800元左右,做得优秀可以晋升为督导,待遇会好一些。”前不久,朱凯和学生们看到一群年幼的孩子独自上、下学,穿越危险通道,便前往探访了孩子们所在的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希望为孩子们提供社工服务,“但是学校并不接受服务,不了解社工是做什么的,认为社工就是志愿者,说‘你们不就是来半天,然后盖个章,拍个照,拿回去换学分吗?这给学校带来很多不方便。’而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看,为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我们杜绝拍照。”
在社会认知度之外,朱凯认为,社工岗位的稀缺及不具竞争性的工作待遇成为社工事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朱凯的学生中有一位男生毕业后在一个社区做社工,“他有心于社工事业,但未来的丈母娘不答应,‘每月一千多的工资,你买得起一平方米的房子吗?’我的很多学生同样面临着十分现实的问题,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学生还能坚持多久。”由此,朱凯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深圳、四川等地社工事业发展较为前卫,多以政府购买的形式运作,对于社工事业在金华的发展,我非常希望政府率先主导,推动行业发展,在民政部门、社区、福利院、学校、医院等单位设立社工岗位,推动社会对社工的接触和认知。”
“社工作为一项舶来品,在国内发展不过20年,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在国内实现本地化应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作为社工,不懈探索,提高自身能力尤为关键。”心理咨询、个案辅导、团队训练是浙师大社工专业学生修习的三大板块内容,区别于心理咨询致力于协调自我及自我与他人、环境的关系,社工更强调整合社会资源,为困境中的人们寻找来自政策、企业援助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只有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才能让社会更认可我们。”
2013年10月29日,在系主任周绍斌的倡导下,浙师大社工系里17位老师每人出资1万元,组建了“金华乐福(love)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八咏楼社区建立了“时间银行”项目,“在项目创办之初,我们借鉴的是上海的做法,由政府主导,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了服务,可以选择把服务时间存起来,也可以兑换为购物券,到社工超市购物。而超市里的产品都是由企业爱心捐助的,很便宜。”但目前项目发展状况并不乐观,“我们在互相鼓励,我的学生们也是一样,在逆境、误解和冷落中保持热情,同时也期待社会各界的支持。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去做正向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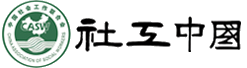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